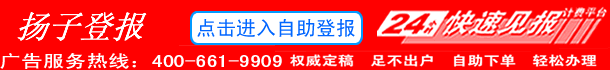赵辰:规划失误是会遭报应的

城西干道改造工程方案”出台后,南京市民议论纷纷,对方案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方案应该走的流程都提出了质疑。日前,快报记者采访了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教授。正在主持南京城南历史风貌区保护与复兴规划的赵辰,结合自己的规划实践,以及国外的先进规划理念,对南京的城市规划,特别是关于城西干道规划的得与失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对自己城市本身的研究不够深入,导致我们的规划缺乏前瞻性。”赵辰表示,不重视规划,或者说失误的规划,是会遭到报应的。
压力重重下的城西干道
星期柒新闻周刊:市建委在上个月底公布城西干道改造方案前,您知道这个改造项目吗?
赵辰:有所耳闻,但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星期柒新闻周刊:之前在电话里,您说对1996年建高架的情形比较熟悉?那您说说当时的情况。
赵辰:我1998年从国外回到南京,当时河西地区正在大规模地开发。我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城西干道的交通问题是和河西的开发有关联的。1998年的时候,包括龙江在内的河西很多地方都开发了。我认为河西大规模的开发会对老城产生非常大的压力。河西离老城太近了,它的面积又非常大。当时的开发项目大部分以居住为主。开发商开发的楼盘就是以离新街口近来吸引买主的。可是在这里买房的人并不都是呆在新区,而大都是往老城跑的,上班啊,购物啊,上学啊。这就导致东西向的交通压力非常大。记得当时汉中路等几条路的条件刚刚改善了一点,但我感觉很快就会不行了。
而河西新区一建立起来,城西干道立即就变成了主轴线。河西的人到老城去,老城的人往河西来,都要通过城西干道。这种进出,并不是通过几个道口就可以实现的,很多人会通过城西干道进行转换。比如住在模范马路的人,到龙江去,他就会走一段城西干道,然后从草场门去龙江。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城西干道交通的压力,主要是来自过江的车辆,南京人习惯从老大桥往返江南江北,而过老桥,必须走城西干道。
赵辰:老大桥与城市的便捷现象,主要是南京的地形决定的。进出南京城,老大桥是最方便的,这一点,二桥、三桥都没有老桥便利。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我认为对于城西干道的交通压力这不是主要的。实际上,河西的开发反而会增加大桥的压力。
规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心太急
星期柒新闻周刊:我们来说说城西干道。建高架前,这条路已经存在了吗?
赵辰:城西干道这条路早就有了,80年代就有虎踞路。虎踞龙蟠,东面有龙蟠路,西边有虎踞路。这是一条小路,而且先天不利。它是夹在城墙与护城的秦淮河之间的,很狭窄,没有施展余地。城东干道,龙蟠路是在护城河以北,也就是河外面的,很开阔。加上南京修复明城墙,城西的这条路愈发狭窄,所以1996年的时候,就决定做立交,做高架。但是高架也要受河与城墙之间尺度的限制。
星期柒新闻周刊:那当初建高架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河的西面去建呢?
赵辰:可能是已经有现成的一条路了,就没想到往西边走。但是做这么大的一条交通干道,应该慎重,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从清凉门往南走,特别明显,河与城墙挨得特别近。
星期柒新闻周刊:当时建高架时显然那条路已经不够用了。
赵辰:那当然了。
星期柒新闻周刊:现在十多年过去,高架又不够用了。当时高架的预期寿命是50年,现在才10来年,就要拆了。
赵辰:高架的寿命,分两块,一块是指高架的交通流量是否饱和,是否能够承载交通的压力;一块是指高架本身,也就是工程的使用寿命。现在看来后者没有问题,问题主要出在交通流量上,这一块的压力显然远远超出原先的设计年限。
星期柒新闻周刊:当年规划和设计的时候,就预计不到当下城市的高速发展,人口的增加吗?
赵辰:总体来说,这种缺乏前瞻性的规划是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个原因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城市本身的研究不够深入,比如说这条路作为小的路没问题,但作为大的路,最好到外头去,到河的西面去做。从历史来说,路肯定应该在护城河外面嘛,闷在里面只能是小路。河西以前一直是江滩地,我们开玩笑,芦蒿就是河西产的。河西不是不可以开发,当初开发的初衷,我想也是为了疏散老城的压力,可是因为开发密度太大,离老城太近,反而对老城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再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城市的发展速度没有准确的预计。南京,包括国内很多城市,发展是爆发性的。我们的汽车特别是私车的发展多惊人啊,速度很可怕;我们交通发展远远跟不上汽车发展的速度。而在美国,人家当年是有规划的,在发展汽车工业的同时甚至之前,就已在发展高速以及城市骨干车型路网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城市原来的基础设施比较差。我们一直都在赶时间,生怕落后了,失去机遇了,有了一个项目,很快就开工了,研究的时间往往是不够的,用南京话说就是比较“吼”。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人家基础设施好,底子好,他们发展就比较从容。
民生工程要尊重民意
星期柒新闻周刊:当初把高架建在城墙与河之间,是不是注定了它被拆的命运?
赵辰:这只能说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要思考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星期柒新闻周刊:按市建委的方案,用隧道代替高架,隧道建成六车道,地上也是六车道,这样,你觉得会改善,或者说改变拥堵的现状吗?
赵辰:隧道的流量肯定要大一点,多一个车道自然会快很多。
星期柒新闻周刊:城市规划应该是规划未来?
赵辰:解决今天的问题,也是规划未来。
星期柒新闻周刊:规划应该是综合工程,其中交通占什么位置?
赵辰:交通规划得好,城市会得益。据我所知,南京市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交通因素考虑得还是不够。我们做规划时,专业的分工分得太清楚了。举个例子,在我主持的南京城南历史风貌区保护与复兴规划,以及上个月底,我们开会讨论水西门地区的景观改造,就涉及城西干道。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城西干道的改造方案,所以我们还是按照高架的条件设计规划的,所以各干各的,是很耽误事情的。
说重一点,不重视交通,会遭到报应的。比如河西这一块,很多人,包括开发商都得益了。可是它造成的交通问题,却是要后人买单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现在城西干道的改造方案一方面正在公示,一方面建设方已经在勘探,据说不久就会开工。国外类似大项目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赵辰:他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规划、开工这么大的项目。在欧洲,这么大的项目,一般说来,十几年前就开始规划了,而且会非常多次地被公共媒体讨论。
星期柒新闻周刊:方案有可能被否决吗?
赵辰:当然可能。
网友
城西干道改造想法“奇特”
23.5亿拆高架建隧道,市民人均支付300多元
城西干道改造想法“奇特”
城西干道改造方案一经推出,在网上引起强烈争议。在西祠胡同“标点-韶韶-记者版”上,争论的帖子盖了600多层。网友“找玩伴”戏称拆除好好的高架建隧道是“奇特的想法”,有网友算了一笔账,花23.5亿重建隧道,按照700万的南京人口数计算,人均要为此支出300多元。
现状
一个骑车人上下班的惨痛之旅
我在新街口上班。1997年底,入住河西凤凰西街,从此开始了惨痛的上下班经历。
1998年 石城桥(现名汉中门大桥)开始施工改造,历经半年架设了一座南桥,这是汉中门地区剧烈演变的序幕。
2000年 虎踞路架设高架桥,汉中门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每天上下班,我在脚手架、噪音、灰尘中穿行,受尽煎熬。
2002年 老城改造开始,汉中路沿途一路开挖,将空中的电缆线埋入地下。我骑车一路磕碰,几乎每周都要去补胎。
2005年 为迎接十运会,这年上半年开始对汉中门大街(桥以西至北圩路止)开始拓宽改造,半幅路面封闭,半幅路面通车,我下班每隔一天都要去汉中门大街上的苏果去购物,于是被迫又投入到拥挤不堪的艰难岁月。
2006年6月 地铁二号线施工开始,汉中路沿途架起了围挡,我又被逼上人行道骑车。
2006年底 汉中门大桥又开始改造,将中桥抬高,南北两桥也加宽。我心想:这种日子要等到哪一天才熬出头啊?
2009年 听说汉中门高架又要拆除了。我无语了。我从三十多岁熬到了四十多岁,现在看来还得熬。网友EOS
争议
堵在隧道里,废气、噪音实在厉害
每天来往大明路和古平岗上下班,虽然走城西干道高架和走城东干道隧道的路程差不多,但实践告诉我,走高架快。高架早晚高峰虽然也堵,但基本上车子都还在动,堵住不动的情况真的很少。早上走过几次隧道,掐着表走的,结果都比走高架时间长,晚高峰更是堵得厉害。堵车的时候隧道里面废气、噪音实在厉害。网友xiao
长江大桥瓶颈不解决,照样堵
想问某些人,你们在拆除城西干道高架的决策上究竟做了多少调查研究。南京到处都堵,难道一堵就要建隧道吗?再说了城西干道也不是一天24小时堵,就是堵也是有原因的,堵的根本原因就是长江大桥的瓶颈效应,长江大桥的瓶颈问题不解决,你就是建十车道的隧道到头来上了长江大桥照样堵。网友DAIXIAOXUAN98
为了高架旁居民?
从赛虹桥到定淮门,沿城西干道两边有多少居民区是有目共睹的。当初建高架是谁不顾市民的反对、不顾两边居民的疾苦,坚持要这样搞“新架坡”的?再者,政府既然已发现高架桥如此恶劣,现在南京为何还在大力兴建高架桥?是局部的闪耀善良,还是在利用善良? 网友爱挂耳朵
支招
盘活存量资产,减少“折腾”
我认为 ,城西干道应该作为“文物”永远保留下来,因为它是我们南京经济腾飞年代的集体回忆。
如果我们的财政一定要花掉这二十三亿才感到痛快的话,也应该着眼于盘活存量资产,而不是瞎折腾。比如:
补贴 由财政补贴长江二、三桥、绕城公路和即将建成的过江隧道,不收费或少收费,势必会分流掉一部分过江车辆。
收费 如果说,长江二、三桥不收费或少收费财政负担不起,那么我们对过老大桥的车辆收费来补长江二、三桥的不收费或少收费,这样虽然有人骂,但分流效果会更好。
疏通 中山南路的一部分已快速化,可否通过建高架和隧道的办法将中山路、中央路、中山北路、中山东路、汉中路等全线快速化,毛细血管通了,主动脉的血才能流得更快。网友扬基佬
赵辰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经先后两次在瑞士联邦苏黎世高等工业大学建筑系深造,也曾在美国及欧洲国家学术交流。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一等奖),建设部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二等奖。
□快报记者 倪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