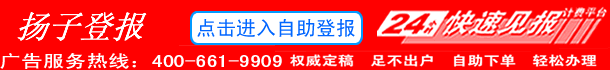贝尔·格里尔斯《荒野求生:贝尔自传》

|
||||||
|
贝尔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冒险家,他曾于英军的特种部队服役,作为一位求生专家,他曾到过和做过大部分常人都未能应付的地方和事情。因其在《荒野求生》节目中所食用的东西太过惊人,而被冠以“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死亡无数次擦肩而过,但结果都是好的 现在的气温是零下二十摄氏度。我甩动着自己的手指,可它们还是冰凉的。旧日的冻伤从不让我有机会忘了它们。我觉得这都是珠穆朗玛峰的错。 “准备好了吗,伙计?”摄影师西蒙笑着问我。他自己的行头已经收拾停当。 我同样对他报以笑容。虽然我其实非常不安。 我有种非常不妙的感觉。但我没理会内心的直觉。是开始工作的时候了。 摄制组其他人告诉我,郁郁葱葱的加拿大落基山今天早上看起来格外壮观。 我脚下是陡峭的山坡。长三百英尺,冰雪覆盖。但我能对付得了。 这种速降我之前就玩过好多好多次了。可直觉在说,绝不要自满。它总是对的。 深呼吸。看看西蒙。默默确认。我跳了出去。急速飞驰的感觉立刻吸引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通常我都喜欢这种感受,但这次我感到不安。 以前在这种时候我从没感到过不安。我知道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的时速很快超过了四十英里。脚踏上了山坡。冰层在我头顶上几英寸的地方擦过。 我的速度更快了。山峰的边缘越来越近。是时候刹住落势了。 我敏捷地往前翻身,把冰镐戳向积雪。一大捧白雪和碎冰高高飞向空中。我用尽全力将冰镐深戳向山体。我能感觉到自己的速度正在急剧下降。 一切如常。跟钟表一样精确。我信心满满。一切都如此清晰明朗。这种时刻十分少有,也转瞬即逝。 它马上就终结了。 我现在静止了下来。 世界安然不动。然后——乒乓!西蒙撞到了我的左大腿上。还有他沉重的木头雪橇、结实的金属相机匣,全都摞了上来。他撞上来的时速有四十五英里。一瞬间,疼痛和噪声伴着白雪炸裂开来。 我仿佛被一列重载火车撞了个正着,像一个布娃娃似的朝山下飞去。 生命在这一刻凝滞了。我觉得看到的一切都在以慢动作进行。 然而在这一瞬间,我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偏上一度,雪橇就会撞上我的脑袋了。毫无疑问,要是那样,“被撞到了”就会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念头。 我大哭出声,流下了宽心的泪水。 我受伤了,但还活着。 我看到一架直升机,但没听到任何声音。然后我到了医院。自从《荒野求生》开拍之后,我已经进了好几次医院了。我讨厌医院。 虽然闭着眼睛,我还是能“看”到它。 越南那间满是血渍的肮脏急救室,我在丛林里切掉了自己半根指头后被送到了那里;然后是育空地区那次坠石事故;更别提哥斯达黎加那次越发糟糕的砾石崩落了;还有蒙大拿的矿井坍塌;在澳大利亚我撞上了咸水鳄;在太平洋里的群岛上,我踩到了一头十六英尺长的老虎;在婆罗洲,被毒蛇咬了一口…… 死亡无数次擦肩而过,但结果都是好的。我还活着。 第二天,我就把那次碰撞丢在了脑后。对我来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虽然发生了事故,但并不是谁的错。 我学到了教训:要倾听自己内心直觉的呼声。 我默默自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世界变得如此疯狂? 六岁时就受到完善的训练:攀爬、悬垂、逃脱 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每当学校放假时都会前往北爱尔兰海滨,去丹纳海蒂镇,待在帕塔夫角的那栋房子里——我的外曾祖父瓦尔特曾生活在此。 我爱死这个地方了。 实际上,我正是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自己对海洋、对荒野的热爱。不过我那时候并不知道。 另一方面,开学以后的日子我就得在伦敦度过。我的父亲是国会议员。 爸爸十分勤奋,经常要工作到深夜。而妈妈作为他的助手,会陪着他一起工作。而我只想要些能和家人共度的时光——平静安然,不慌不忙。所以我时常反抗他们。 这可能就是我会在学校表现那么糟糕的原因吧。 记得有一次,我狠狠地咬了另一个男孩,咬出了血。然后我看着老师给我父亲打电话。我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打得我屁股开花。 第二天早上,我在伦敦市一条繁华的大街上挣脱了母亲的手,跑掉了。几个小时后我被警察找了回来。我估计那是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吧。 我母亲之后不得不把我锁在卧室里,免得我再捣蛋。可这样一来她又会担心我有可能窒息。于是她让木匠在卧室门上开了几个气孔。 有道是,需求是发明之母。我很快就发现,把一个衣架掰弯之后,我就能通过气孔把插销弄开,然后逃之夭夭。这是我初次涉足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世界。类似的技巧多年来对我都很有帮助。 在这段日子里,我还发展出了对于运动的热爱。 妈妈每周都会把我带到一家培训运动员的小体育馆。那里的馆主斯特吉斯先生将军队中铁一般的纪律带到了他的培训课堂上。感觉似乎斯特吉斯先生忘记了我们才六岁。 我那时就受到了完善的训练:攀爬、悬垂、逃脱。 少年时代的我热衷于所有的旅行——只要和爸爸一起。 我记得跟爸爸一起在冬天攀岩的快乐。每次攀岩都是一次冒险。我喜欢爬到悬崖顶上,然后回来时浑身泥水,上气不接下气,自己回想刚才都有些后怕的感受。我学会了享受风雨扑面而来的感觉。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大人,尽管实际上我还只是个小男孩。 有一回我们去了英国一个一年四季都荒无人烟的地方:达特穆尔高地。 那时候已入深冬,地上满是积雪。我现在还记得每天出门时外面有多寒冷刺骨。 我小时候的那张娃娃脸真的是被冻成冰块了。我的鼻尖完全失去了感觉,这是个怪吓人的全新体验。我哭了起来。这通常都能让爸爸发现情况严重,引起他的关注。但这次他只是对我说:“裹严实些,坚持住。我们正在进行真正的探险,没时间让你哭哭啼啼。不舒服忍忍就过去了。” 于是我闭上了嘴。他是对的:过了一会儿就没啥感觉了。我小小的心灵里为自己能忍耐过去而感到骄傲。 加入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前的选拔测试 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誉满全球。它以冷酷、高效、高度专业军事化而闻名,世界上其他的特种部队都以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为蓝本。它的成员选拔过程是艰苦而漫长的。每十个申请者中大约九个都会被刷掉…… 我十六岁时已经通过了皇家海军陆战突击队的预备军官训练课程,毕业之后就能成为一名青年军官。 但我心里还是有些犹疑。我在加入皇家海军陆战突击队之前,是不是至少该试着参加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预备役的选拔测试? 我确认,我至少该去试试。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我站在了兵营大门口,手里拿着召集令,紧张不安。 他们首先想要筛掉那些毫无机会通过的人。 他们有个特别可恶的把戏:让我们全都在一个小山包顶上站好。小山包很陡,大概两百英尺高。然后他们会让大家全都下山去,叫我们扛起自己的队友,然后宣布最后回到山顶的两个人会“被遣返原单位”,也就是失败了。然后除了最后一组那两人之外,所有人又都被赶回山脚,再来一遍——然后再来,再来。直到剩下的人寥寥无几。 很快我们这支队伍已经减员接近四分之一了。现在我们要正式开始进入选拔测试了。 整个选拔的第一阶段,“山地”段,都在威尔士荒无人烟的布雷肯山区进行。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相当多时间都在这片山区里汗流浃背地挣扎。先是在闪耀的阳光下,顶着不断上升的温度,周围的蚊子多得成灾。汗湿重衣;然后季节变换,我又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蹚路,身上又冷又湿;有时候高峰上的狂风几乎要把我吹倒在地。我们多次都要带着总重达七十五磅的行李——跟一个普通八岁小孩的体重差不多。 山路越来越陡峭,我的体力枯竭得也越来越快。我不停地告诉自己:绝不能松懈,只要松懈一下,我会被其他新兵淹没。在越来越让人痛苦的坡度和速度面前,这种可怕的前景给了我力量,让我坚持向前。抵达峰顶的时候,我发现我周围已经没几个人了。 接下来的行军难度继续加大:距离更长,负重更高,压力有增无减。除此以外,每次行军我们都是分开来单身上路,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开始检验我们独立工作的能力了:在山区找到道路;带着负重;按时到达。 没过多久,我们连队里的新兵数量就减少到不足十人了。 最后的测试周就剩下三次行军等着我完成了。 但每次都难度极大。 凌晨两点,我被我的闹钟惊醒了。 我觉得自己身上累得厉害,我的脚踝和脚掌也都肿得厉害。我顶多只能一瘸一拐,真的是一瘸一拐,慢慢走到一百码外的食堂去。 二月的午夜,空气冷得让皮肤生疼。我们在黑暗中站好队列,一片死寂。没人说话。 我们的背包现在重五十五磅,外加武装带、饮水、食物和武器。太重了。 最终,我听到了我的姓名。 “格里尔斯,开始计时,去吧。” 我越过小路,走进夜色中。 我在山峰顶上的第一个三角测量点确认了一下自己的方位。我判断我可以抄个近路,直接穿过山谷中央,而不是沿着外缘绕路。 很快我就知道这是个错误。 我大大低估了积雪的厚度。但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沿着这条路走出太远,无法回头了。被吹到谷底的积雪厚得可怕。我在齐腰深的雪层中移动的速度跟蜗牛差不多。我能看到上面有一行人的身影出现在被满月照亮的天际下,是所有其他的新兵。与此同时,我则在这片深雪地狱中苦苦挣扎,不得寸进。 我独自一人落在了后面。我朝山上爬去。风大得可怕。我真的是在进两步退一步地爬。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山梁上狭窄的小路前进,右边几码处就是大约八百英尺深的峡谷。 我脚下一小片结冰的水洼忽然间裂开了。我掉了下去,大腿以下都浸在了徐徐渗出的冰冷的黑色泥浆中。我身上都湿了,而且盖上了一层沉重的黑色黏土。它们好像粘在我腿上了。 当第一缕晨曦升起之际,在这个富于象征意义的最后一个早晨,我恰好爬上了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一座高峰的东面山梁。 我们今天一整天都要走个不停,一直到次日凌晨——如果我们能完成耐力行军的话。 我只能继续缓步前行,继续,再继续。这是一场战斗,我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在不断被消耗,同时我还要一直努力无视进了水的破靴子里我受伤的双脚越来越强的胀痛感。 我又爬下了一段冰雪覆盖的陡坡,来到了一个水库旁。这里是我们行程的中点。 我能看到几个别的新兵。他们正一边拖着脚离开检查点,一边没命地吃着东西。 又走了十英里之后,我追上了我的好朋友查克。我们一起继续向前——两个孤独的身影,奋力对抗着体力的渐渐枯竭,尽力保持速度。 很快天就完全黑了,山里的雾也越来越浓。能见度几乎降到了零。 忽然我滑倒了,然后开始沿着脚下满是泥水和冰雪的凹槽迅速往下滑去。查克紧跟在我身后,他也掉了下来。 我们在半泥半雪的脏雪堆中慢了下来。我转过身,准备爬回刚才滑下来的地方。就在这时我们忽然看到就在下方不远处有一点灯光。我意识到那正是我们一直没找到的检查点。我们绝望的无声祈祷得到了怎样神奇的回应啊! 我们在检查点登记完毕后就朝着最后一个会合点出发了。 忽然之间继续前进几乎不可能了。我连着三次陷入齐腰深的沼泽中。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砍伐后留下的树桩,而且它们还半埋在泥雪中。 我冻得要死,而且严重脱水了。这次行军快要击垮我了。 我已经黔驴技穷了。我正不可挽回地渐渐无力动弹,因为我太累了。 我们连队里的另一名新兵马特这时也跟我们在一起。他看出我已经到了极限了。他把我拖到路边,给我多盖了一层衣服。他把自己的水分给我喝了些,扶我站了起来。 然后,我们三个一起继续向前…… 终于拿到那顶梦寐以求的贝雷帽 回到军营里时,我们这些还没被淘汰的人脸色苍白,走路都颤颤巍巍。但我们如释重负:严酷的考验终于过去了。 我站在那儿,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靴子,靴子上满是裂口和泥巴;我的裤子破了好几处;上身衣服满是汗臭。但我这辈子从没感到这么自豪过。 我们所有人都自动立正——荣誉上校跟每个人握手,然后我们终于拿到了那顶梦寐以求的贝雷帽。 可一路走来,我已经明白,重要的绝不是这顶贝雷帽,而是它代表的意义:战友情、汗水、技术、谦卑、忍耐,还有个性。我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戴到了自己头上。 荣誉上校走完了我们的队列,然后他转过身说:“欢迎加入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