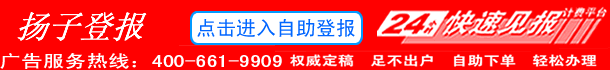回 家

吕清泉
他是我在ICU接手的一个病人。七十来岁,肺栓塞。他插着呼吸机,但神志清醒。清醒到足够决定自己的生死。
第一天送他过来的时候,儿子说:“尽全力抢救。”在ICU里待了三五天以后,儿子问:“医生,老爷子这个样子,有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呢?”第一天是情感。三五天以后,落回现实。先不要去批判儿子,把一切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好像我们拥有那种审判的权利,又好像只有审判别人,才能豁免自己。何必呢?如果足够富裕,又或者,如果老天爷足够仁慈,谁会愿意置身于那样的一种选择之中:坚持或者放弃,筹码是,亲人的生命。
有一天下午四点,老太太进来探视。她穿着隔离衣站在床边,俯身问老爷子:“你想回家吗?”
老爷子戴着气管插管,点点头。老太太红着眼睛问:“你要回哪个家?江宁那个家,还是咱们老家?”老爷子挣扎着抬抬手,指了个方向。老太太心领神会:“你想回沭阳,还是啊?”
老爷子点了点头。
第二天,家里人叫了120,来接老爷子回家。儿子问:“拔了管,能撑到家吗?”我们告诉他,勉强可以撑到。儿子问:“医生,还能在这给他把衣服穿好啊?”那个衣服,叫做寿衣。老爷子要穿好衣服,回家去的。隔了些天,儿子来办出院手续的时候说,老爷子已经走了。一个毫无悬念的结局。
我们说:节哀。
下午四点,门外柳树上西沉的太阳,色泽浓烈而温和。我坐在电脑前写病历,却不停地想到那个问题,老太太问老爷子的那个问题:“你想回家吗?你想回哪个家?”我在心里,替几十年后无力答复的自己,悄悄地回答:“我想回有爸爸妈妈的那个家。”如果分离意味着另一场团聚,那该多好。
还是会想到那个老爷子,想起他那天穿戴整齐,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样子。会想到生命给人太多的惊叹。譬如新芽破土,譬如草木凋零。譬如沧海桑田,譬如暗流汹涌。那些不为眼见耳闻的事件,却又会在某年某月某天,突如其来地出现在眼前,像一场密谋。譬如,一套寿衣。从来没有哪个老人会在你面前提起。可他们却会不约而同地,给自己备好这样的一套衣裳,给自己一个体面的落幕。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他们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老”的?他们得到老天这样一种昭示后,要怎样面对那种无可倾诉的惶恐?他们在临终时,最希望被怎样体贴地照料?
没有答案。
以我贸然的猜度,却总是觉得,回家,终归远胜于拖着气管插管,流着口水,苟延残喘吧。可那种时候,还能有多少人,能颤巍巍地抬起手指,坚定地指出回家的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