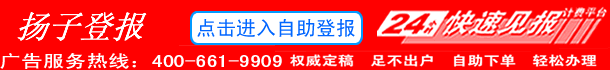电视选秀第八年“回潮”:将死未死 出路在哪



中国的电视选秀舞台从2003年拉开大幕,第一年,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第二年,大家开始翘首以盼,第三年,举国狂欢,第四年,质疑纷纷,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所有人都在说,选秀沦落成了一个怪物,选秀将死。
然而,第八年了,它并未真正死掉,相反,在今年来了次“回潮”。有人认为,2011年很可能是选秀节目一个新的转折点。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被群攻这么多年仍然不倒?这一次,是重振雄风还是垂死挣扎?在第八个年头上,选秀节目又一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将死的选秀?
几千个女人啊,太壮观了
4月22日,湖南广电职工活动中心篮球场,《快乐女声》长沙赛区第三次海选。张渊(化名)一大早就到了,作为宣传人员,他必须每天来“盯场”,按经验,他估摸今天又得忙到晚上7点以后。
活动中心的篮球场上,除了络绎不绝的报名者,还有准备参加这次海选的选手们:四周观众席上坐满了年轻的女孩,间或有大妈和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鲜亮的服饰和明晃晃的笑容,让硬朗的球场一下子沾染上“歌舞升平”的味道。观众席是不分座的长条凳,一批人走了一批人再填上,忙得晕头转向的张渊偶尔抬起眼来看一圈,忍不住在心里感慨:几千个女人啊,实在太壮观了。
工作人员不时来观众席领人,点到名的候选者排着队,穿过球场,进到旁边的十几个试唱间里,在评委面前唱上一段,再出来。在等待自己人生第一场选秀比赛的过程中,大多数选手互相攀谈起来,耳语、轻笑、不时连成一片的响亮歌声、偶尔爆发出的叫好和掌声,整个场子嗡嗡作响,蒸腾出某种混合着兴奋、紧张又期待的情绪。
三次海选,张渊被选手的热情一次复一次地感染着。看着眼前的景象,他没有办法将其与“选秀已死”的说法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选秀的生命力明明就像那些歌声一样,不仅蓬勃,而且连绵不绝。
不论主办方们是不是也这么想,事实是,走过“七年之痒”的选秀节目,似乎在第八个年头上迎来了“回潮期”:湖南卫视的“快女”复活,青海卫视的“花儿”、东方卫视的“达人”和江西卫视的“红歌会”去年余威犹在,山东、东南、辽宁卫视等又先后加入战团。虽然比不上鼎盛时期大大小小十几台选秀打擂的盛况,但和去年只有四五家还在惨淡经营相比,今年选秀节目确实回温明显。
然而,与张渊和他的同事们一腔热血相对的,是其余各方力量的冷眼。“你还会关注今年的选秀吗?不关注,请一针见血说出你的理由。”前不久,娱乐评论人“舞美师”在微博上放出这样一条小调查。短短几天,该微博的评论已经达到1400条,被转发近700次,绝大多数网友明确表态:“不看。”
拒绝的姿态已经不算什么。从2006年选秀节目收视走弱以来,年年选秀,年年媒体和专家学者们都要出来骂一遍,“跟风”、“恶意炒作”、“庸俗”,几乎成了选秀三宗罪。广电总局也从2007年开始不断出台严控措施,不能黄金档播出、不能投票、不能煽情、不能毒舌,掐在选秀咽喉上的那只手越收越紧。
“选秀将死”的论调唱了这么多年,疾言厉色的批判持续了这么多年,选秀节目一副气力将竭的模样也拖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未曾真正死掉,反而在第八年上来了一次“反击”,究竟何解?
没人看的选秀?
一茬又一茬,粉丝总在产生
2005年的夏天,无数少男少女为《超级女声》疯狂,网友“我是天然呆呆呆”也是其中之一:那年她13岁,最喜爱的选手是何洁,所有比赛她从头看到尾,一场没落,还“疯了一样发短信投票”。那一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花落李宇春,“粉丝”的概念爆炸性传遍祖国大地,选秀节目也随之迎来全面鼎盛时期。
6年后,李宇春还叱咤于歌坛,何洁和一大票选秀歌手却早已泯然众人矣,那一代“超女”辉煌后,选秀节目再也没有出现过足以震撼娱乐圈的人和事。而19岁的呆呆不再看任何选秀节目,也不准备看今年的《快乐女声》,在“舞美师”的微博调查底下,她言简意赅地给出了如下理由:“一,审美疲劳。二,质量下降。三,炒作太多。四,个人认为《非诚勿扰》的两个光头更有内容。五,自己成熟了。”
呆呆的观点暴露出选秀近几年的致命伤:模式单一、制作粗暴、黑幕众多、炒作太过……每一条都足以成为观众“嫌弃”的理由,综合起来,就是一档选歌手的节目,最注重的不再是唱功,而是收视和话题,浮躁之气尽显。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谈到这个就摇头:“我曾经被某些选秀节目请去做策划,去了一看,这么大的新项目,什么问题都没想明白,就要上马,做出来的质量,能看吗?”
浮躁的不仅是活动主办方,选手参赛功利化,这也是选秀节目被诟病的一大原因。刘家仪(化名),北京演艺专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大二学生,目前正在全力备战“快女”。但她并不算白纸一张的“素人”:参演多部电影,出演舞台剧,拍摄世博会宣传片,21岁的她甚至已经签约了演艺公司,发过一张个人单曲。她还参加过去年的“花儿”,并进入了广州唱区50强。
这种情况在家仪的同学中不算新鲜事儿,大家把选秀当做功课或者考试一样一次次认真准备,“有参加‘快女’的,‘花儿’的,还有金钟奖,最近校园里谈的都是这个,气氛挺紧张的”。她觉得这没什么,“选秀不也是锻炼新人的舞台吗?这些都是我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而已。”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出名而唱歌,而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网友“谢谢晨晨”感慨。究竟是心怀音乐梦想,还是想一夜爆红做明星,这些年轻人为何而来其实并不重要,事实是,他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选秀可以上升为进入娱乐圈的一条捷径。
而在呆呆的同学中,绝大多数人都和她一样,这群当初为选秀节目痴迷的孩子自认已经长大,更理智,也更清醒,“再看那种东西太丢人了”——选秀在他们的嘴里逐渐演变为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贬义词。对于被生活所累的成年观众,需要倾注狂热的选秀节目更从来不是一个主流选项,有调查显示,选秀节目的观众年龄主要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其中又以16到18岁的观众集中度最高,女性、学生的标签也大大超过其它关键词,换句话说,“低龄化”和“少女化”决定了选秀节目的主流观众并不会是电视的主流收视人群。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选秀节目中“偶像文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也印证了像呆呆一样的观众的离开。不过,它同样也暗示了,新的观众将不断成长起来,弥补上一代“粉丝”离去的空位。“我们就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定位观众,一茬长大了,另一茬又长起来了,新粉丝每年都在产生。”某选秀节目负责人说。 “选秀不是一个怪物。”李忠敏(化名)总是试图跟大家解释,他是某卫视著名选秀节目的高层之一,深知在今天的大众眼里,选秀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三俗”,上头不喜欢,下头又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唾弃,收视报表一年比一年难看,这样畸形的节目,何必还做下去?
但是站在一个电视人的立场,一个活动主办者的高度,看到的景象却全然不同。这也是李忠敏在“怪物”之后通常跟着的一句话:“它是一种方兴未艾的、优质的节目类型。”
做了14年电视,李忠敏自认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电视人。这种责任感,体现在选秀节目的“使命感”上:“国内的演艺市场,目前较正式的出口还是只有专业学院,低端的出口相对匮乏,这是选秀存在的最大意义。”湖南卫视对此有着一番相似的解释:“音乐是人类不变的需求,每年都有热爱唱歌的人们需要有舞台给他们展示。所以只要音乐还存在,爱唱歌的人还存在,选秀就会被需求。”
但责任感并不能解释所有动机。“收视,吸金能力,品牌效益。”李忠敏坦然给记者开出一张选秀节目的利益诉求单。2005年,《超级女声》创下平均8%-10%的收视神话,而去年的“快男”10进8的收视率却不到1%,相比巅峰期收视下降了近九成。尽管如此,比起其他综艺类型,选秀节目对收视的绝对拉动力仍然不可忽视。“吸金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广告收入,去年第一次搭台的“花儿”,造价1000多万元,入账7000多万元,差价6000万元,而收视率看似惨淡的“快男”,净赚广告费就有一个亿,“就算口碑、人气大不如前,赚钱根本不是问题”。除此还有对品牌的提升力,“到哪里去找一个大型节目活动,能像选秀一样,短时间内迅速积聚如此多关注和人气?” 面对大众对选秀的种种指摘,李忠敏有些委屈,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总是“边骂边看”。“他们没有从节目中获得快乐吗?”他连续反问,“这种强有力的互动性,全民参与所带来的快感,除了电视,哪种媒体可以做到?”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也默认这一点,这种互动甚至把从前很少看电视的青少年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拉”了回来,重新吸引到电视机跟前,相当于,选秀“没有从原有的蛋糕上分走更多,而是另外做了一块蛋糕”。
虽然不是怪物,李忠敏也十分清楚选秀的弊端,他认为电视人正为此努力:青海卫视要办遗珠唱区、高校唱区,湖南卫视搭上微博新媒体,东南卫视则干脆放弃个人赛,转投团体赛制……一切的一切,都透露出这群电视人转身起跑的迫不及待:“创新,一定要创新,不然还是死。”
这种充满主动性的解释,在张颐武看来,却是选秀节目发展至今的顺势之举。“选秀节目的造星任务已经结束了,下一步就该发展到平民表演为中心。”他把相亲类、求职类等近两年兴起的综艺节目,也看作某种程度上选秀节目的“变种”,“核心主打的都是‘秀’的精神,只不过秀的途径、方式和目的不同而已。”
一片讨伐声中,李忠敏颇有些孤胆英雄般固守着自己的信念,他把选秀比作一场大戏,曲折、反复,充满变数和意想不到,即使一时演得不好,却可以打动很多人,甚至改变其中一些人的人生观和命运,“你觉得,这样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节目,不值得坚持吗?”
李宇春式的造星神话只有一个,对于更多的选秀歌手,当舞台的灯光渐渐暗去之后,不少人又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还在娱乐圈飘的,或坚持音乐之路,或把重心逐渐转移到演戏、主持等方面。对他们而言,选秀歌手或许是个让人尴尬的标签,但无人否认,选秀也拉开了他们生命中最大一次转折的闸门。
下一个18年还可以有别的辉煌
王啸坤,2006年18岁时东方卫视《我型我秀》总冠军。他回忆总决赛后被威亚吊着飞起来的那一刻,“感觉人生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世界全在自己的脚底下”。其后,他签约环球唱片公司,发单曲、发专辑,商演不断。每天晕晕乎乎地跟着公司安排走,某一天,他突然惊醒:“我想要的不是做艺人,而是做音乐;我希望自己是个创作型歌手,不是明星歌手。”
2009年,王啸坤与公司解约,成立了自己的厂牌,“做自己想做的音乐、签乐队、参与MV制作、发潮牌,一切都很新鲜!”现在的王啸坤被标榜为“独立音乐人”,当年的选秀经历已很少被人提起,音乐和品牌却越来越为推崇个性的小众群体认可。
回头再看选秀,王啸坤仍然感激那次改变自己生命轨迹的机遇:“但那只是人生第一幕的高潮。下一个18年,我还可以有别的辉煌。”
陈西贝,2005年《超级女声》成都唱区第七名。赛后签约天娱公司,不过,她很清楚自己志不在唱歌,“我想做个演员,不想只是个‘超女’。”她一度十分反感“选秀歌手”的标签,在天娱时,拼命跟公司争取演戏机会,后来又跳到更专业的影视公司,希望用影视作品淡化身上的“超女”标签。
但事业并不如想象得那么顺遂,陈西贝拍了十几部电视剧,还参演过电影和话剧,没有遇到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角色,大家提到她,最常用的标签还是“超女”。
陈贝西很平和地接受了这一切:“当年我们班上30多个同学,如今只有我一个人真的成了演员——选秀起码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她还调侃自己不温不火的状态,“我是走在队伍中间的人,中间的风景也很美啊。”
还是靠实力和作品说话
大春子,2009年《快乐女声》全国第十一名。大春子赛前就灌录过自己的发烧碟,在爵士乐圈小有名气,赛时更被专业评委惊为天人,实力强而形象不佳,她的被淘汰在当时被不少人看作比赛有“黑幕”的有力证明。
赛后,大春子和其他17名选手一同签入天娱公司,艺人实在太多,爵士乐市场不佳,加上个人形象缺少优势,结果她成天跑场子,一张单曲未出。一年后合同到期,公司也没有挽留的意思。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忽视,大春子什么也没说,只反复强调一句话:“‘超女’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选秀就是一个年轻人追梦的过程,自己坚持才最重要。”解约后,她认识了一批圈子里的音乐人和制作人,选秀时的不少歌迷也默默一路相伴。
眼下,她正忙着一出音乐剧的排练,自筹专辑也进入挑歌阶段。专辑中有一首歌,原作就来自比赛时支持她的一位歌迷,“一个深圳的爷爷,自己谱曲写词,经常把乐谱和自己录的小样寄过来给我。”大春子丝毫不介意被贴“快女”标签,因为她知道,“到最后,还是实力和作品说话”。 《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由福斯广播公司从2002年起主办的美国大众歌手选秀节目,原型为英国电视节目《流行偶像》(Pop Idol)。节目一经播出就获得超高人气,近年的收视率牢牢占据美国黄金时间段电视节目榜首。《美国偶像》也被认为是中国众多选秀节目的始祖,早年“超女”就曾一度陷入山寨“美偶”的指责中。
作为一档全民娱乐的电视真人秀,《美国偶像》的评委基本固定,为两男一女,评委在各大州进行初选,通过的选手集中到好莱坞参加下一轮比赛。半决赛共有24名选手(12男12女),由观众电话或短信投票,得票最低者陆续被淘汰,最后的胜出者就是“美国偶像”,奖品是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
《美国偶像》在美国引发的全民狂热是谁都没有预想到的,一届比赛可以收获超过5亿张选票,高出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总统选举的投票数。
但《美国偶像》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收视率下降是近年面临的现实。不过,其成熟的商业运作,精良的制作班底,高素质的评委队伍,和“美国梦”的打造模式,仍然被认为是无可替代的。有人评价国内选秀与“美偶”的差距:“别人单宣布结果就能制作成一小时的节目,而且跌宕起伏,精彩纷呈,这种功力国内电视人难以企及。”